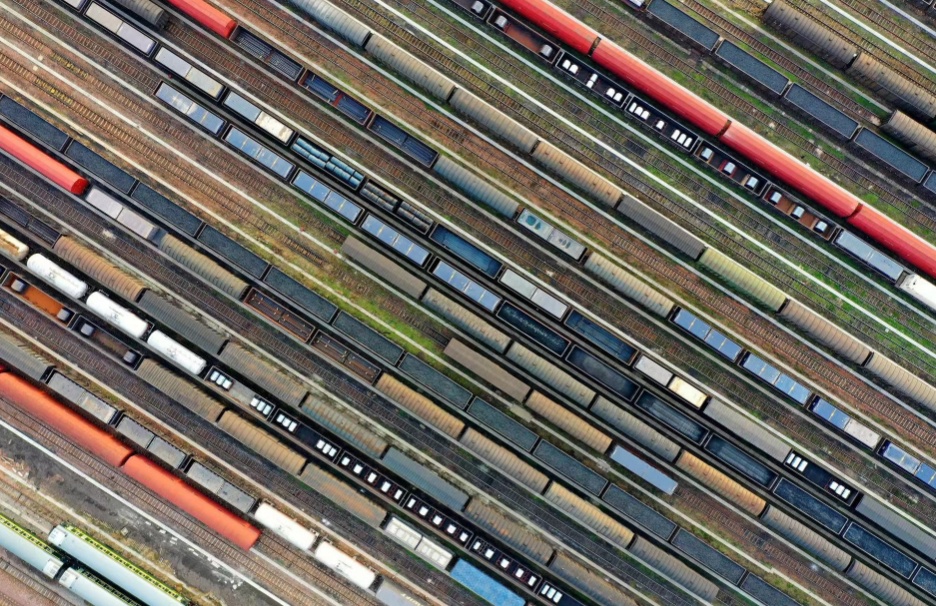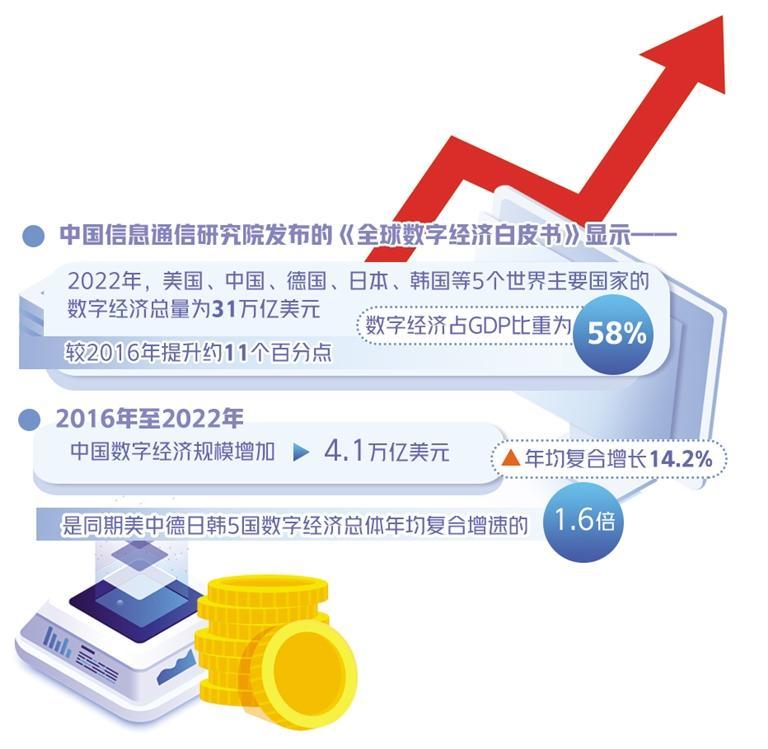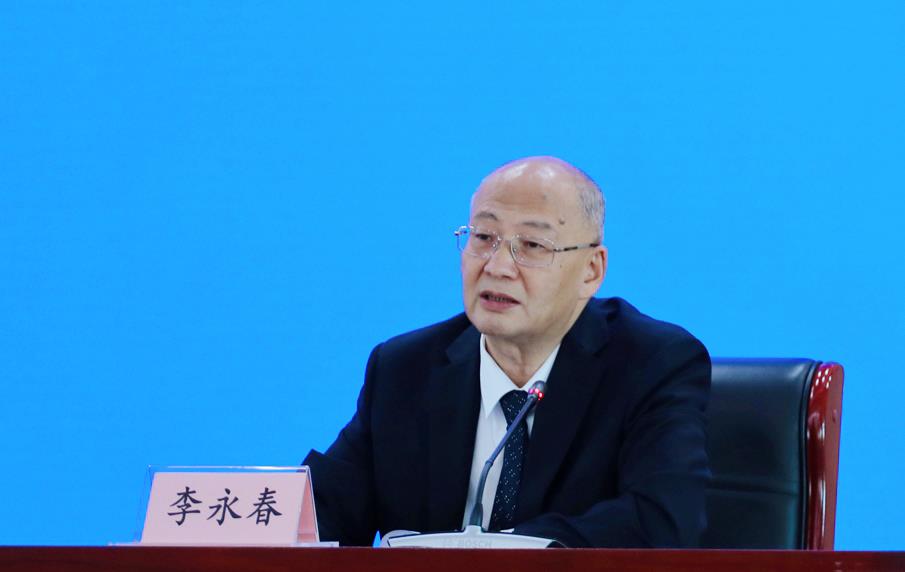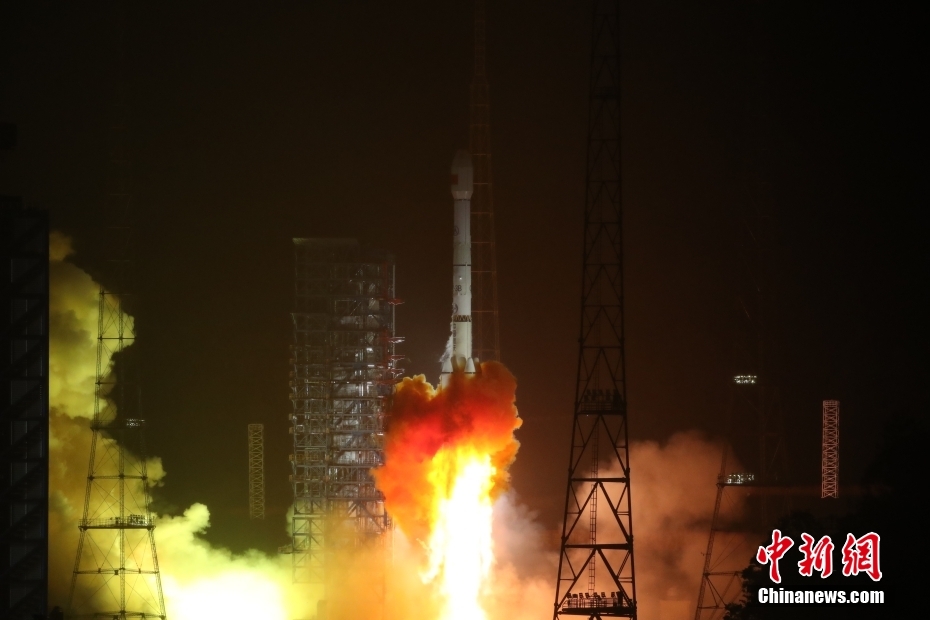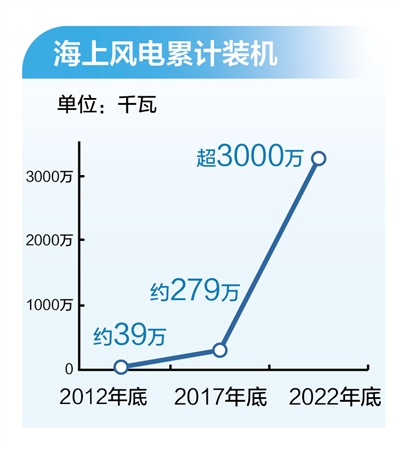作者:吴聚平
“很久没有吃过这样的猪脚汤米粉了,那股辛辣的胡椒味中夹杂的独特猪杂骚味,恰到好处地勾起过去的味蕾体验。下汤的猪脚不能太瘦,一定得带一两块肥肉,不能吝啬胡椒,盐也要稍微重手一点点,这样汤就丰满而不腻,再加上灵魂伴侣小葱花,让身体与灵魂都得到了最好的安抚。”
 【资料图】
【资料图】
2020年冬天的一个早晨,我在朋友圈里写下这段文字。那是我回到这个县城生活的第一个冬天,在屋外呼呼的冷风中,我在早餐店干下一碗久违的猪脚粉,打着饱嗝,写下了这段感慨。
那时的我不用赶时间,也不打算为了一碗粉以外的事情焦虑。早上七点多,在把孩子送到幼儿园后,就开始穿过小区大门,往两百米外的东源市场走去。驼色大衣迅速地融入一片五颜六色当中,我像个颇有经验的主妇那样,蹲下身子,向摆摊的大妈问询一把芥菜的价格。
过去十年中,在同样的时间段里,我是一个脚踩高跟鞋,奔波于地铁、高楼、写字间的职场人。这样的切换,让我一时感到恍惚。我是谁?我在做什么?
对于人生的选择,或被动或主动,都不是一时兴起,而是辗转后的决定。那些高级写字楼里的岁月,时间以一种恒温的方式存在。冬天和夏日在那里没有很大不同,早晨与下午都是灯光通明,你所面对的是屏幕、上司、会议、绩效。结束一天工作后,人群像水流一般汇入夜色,挤进车厢,我的驼色大衣如同汇入一片荒漠。而此刻,在通往菜市场的路上,我的身心是放松的,眼前是新鲜的菜蔬与小贩尽力的吆喝,是热乎的世俗的温度。
一碗猪脚粉,通过味蕾,唤起了我最切实的乡愁。
二十多年前,为了更好的生活,许多乡亲来到河源城做生意,贩卖青菜,开猪肉档等。父亲也和这些乡亲一起,来到了当时的河源老城上角市场。每天早上我和妹妹还没有醒来时,父母就早已经出档了。等到日头升起时,我才和妹妹走一段小巷,到肉档去寻找他们。
上世纪90年代河源城的早市热闹非凡,还没到肉档前,已经远远闻到一股猪骚味,它的浓郁充满着食欲的诱惑,而葱花的味道,像跳跃的音符,在骚味上来回点缀,唤醒了市井人群所有的生机。等我走到档前,那些猪肉档老板便问着父亲,“把大阿女也接来了?”父亲应着,拿两个大碗,给我和妹妹打猪脚粉。在粉的上面,再满满地覆盖上一圈瘦肉、猪肝与粉肠。
在这个日新月异的时代,一切都在迅速改变。当年出城创业卖猪肉的乡亲们,大多已在城里置业、安家,并说着一口带源城口音的客家话。而父亲则回到了老家,开始烹饪自己的那一碗猪脚粉。
这些年,我们带着孩子回到老家的时候,早上还没有起床,就已经闻到了厨房里传来的猪骚味和胡椒粉的味道……




















![蝉声荷色动清吟[古韵今声]](http://imgs.hnmdtv.com/2022/0610/20220610022616761.jpg)
![蝉声荷色动清吟[新诗之页]](http://caixunimg.483.cn/2022/0610/20220610014037353.jpg)
![蝉声荷色动清吟[会员风采]](http://www.lygmedia.com/uploadfile/2022/0923/20220923103853871.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