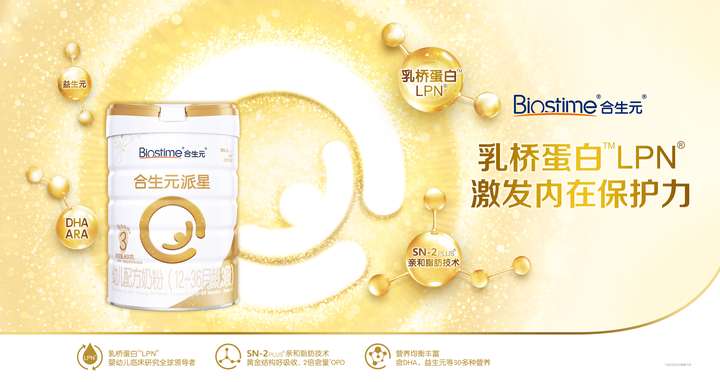(资料图片仅供参考)
(资料图片仅供参考)
作者:吴征(Jason)
今天偶然读到IPWatchdong上一篇发表于2018年的文章,内容颇有意思,其中的提问值得今天的中国在思考如何处理NPE问题时进行借鉴。
以下我将这篇文章的大致内容和对中国的思考做一些简述。
这篇文章的名称是《开国元勋关于促进NPE和专利许可的决定》,作者是大卫·克莱恩(David Kline),这篇文章是节选自他的一本书中的一部分,这部书的名字是《无形优势:理解新经济中的知识产权》。
首先来看一下本书的作者大卫·克莱恩,他是普利策奖提名的记者、作家和传播策略师,曾为世界上许多最重要的知识产权公司提供咨询。他在哈佛商业出版社出版的畅销书《阁楼上的伦勃朗》被认为是美国企业专利战略的开创性著作。克莱恩被IAM杂志评为世界300大知识产权战略家之一,他还是《无形优势:理解新经济中的知识产权》的作者,这是第一本面向普通(非法律)受众的知识产权教科书。
再来看一下IPWatchdog这篇节选的文章中,讲了哪些内容。实际上,从这篇题目中,也可以猜得到,文章重点说了两部分内容,一是NPE,二是专利许可。
的确,大卫·克莱恩认为,历史上正是因为美国专利制度对于其学习的英国专利制度的这两点改造:一是没有“制造要求(working requirement)”,二是专利被视为可以出售的资产,使得美国创新很快就超过了英国。
首先,对于没有“制造要求”方面。
在关于HR-41的辩论中,“参议院建议要求专利权人根据该专利制造产品,或许可他人这样做。但众议院认为这是对专利权人权利的侵犯。”HR-41法案于1790年成为美国第一部专利法。
也就是说,美国的开国元勋们认为,“制造要求”只会加强垄断力量,并通过将专利限制在那些拥有制造其发明产品所需工厂(或建造工厂的资本)的人身上,使发明向现有行业倾斜。 大卫·克莱恩甚至认为,正是美国的开国元勋创建了现在所说的“非实施实体”(NPE),从而来扩大当时落后经济中的发明家库,从而涵盖了没有财富和资源将自己发明商业化的普通公民。 这一举措导致了19世纪美国的创新激增,因为大量普通民众开始发明,然后将他们的发明授权给企业进行商业化。 从数据来看,到1865年,美国的人均专利拥有率是英国的三倍多,到1885年,是英国的四倍多。 其次,专利作为可转让资产大卫·克莱恩认为,对美国经济增长影响最大的一个特点是“法院和美国专利局都为出售专利权提供了明确的规定。” 他认为,这样做使得没有资本将自己的发明商业化的普通工人或农民发明家,仍然可以参与发明活动,并通过向有能力的企业许可或出售专利来赚取收入。这种许可专利权的能力(加上低廉的申请费)使发明成为成千上万贫穷但技术上有创造力的公民的新职业道路。它还被证明是调动资本投资于新技术并将其商业化为社会新产品和服务的有力手段。 专利可以被非执业实体用作可交易资产,而这些实体没有财富将自己的发现商业化,这是美国专利制度的一个完全独特的特征。到1880年,85%的美国专利是由发明人授权的,而英国专利的这一比例为30%。 例如,根据美国贝尔公司1894年的年度报告,该公司的研发部门从外部发明人那里获得了73项专利,而自己的员工只开发了12项。 他在文章中提到,学者们发现,专利许可是由一系列中介机构——律师、风险投资家和专利许可代理人——为专利技术的交易和商业化“降低了交易成本,提高了效率”提供便利的。“通过使发明家能够,甚至鼓励他们专注于他们做得最好的事情[即发明],这种分工产生了美国历史上技术最丰富的时期。”
所以他认为开国元勋培育非营利组织和专利许可的决定对美国的快速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至关重要。 并且援引19世纪的专利记录,工业革命中超过三分之二的“伟大发明家”,包括托马斯·爱迪生和埃利亚斯·豪,都是专门从事发明并将部分或全部专利授权给外部企业开发新产品的NPE。 因此他坚定的认为, 如果美国遵循旧的欧洲专利制度,将专利权仅限于制造或销售产品的发明人,或者阻止他们获得专利许可,那么美国甚至可能不会发生工业革命。因此,他认为这种将发明和生产之间的分工,成为有创造力的个人越来越关注其比较优势的一个很好范本,极大的促进和鼓励了美国初期独立发明人的蓬勃发展,使得发明活动变得非常普遍,带来了社会的整体创新。 结语:对中国的启示当然,我们不能否认这篇文章看上去属于美国支持专利强保护一派,以及鼓励独立发明人和维护NPE行为合法性的支持者的声音。 但是如果我们从客观的角度去思考,是不是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美国有别于英国的这种模式确实能够促进社会的整体创新呢? 其实,从他提到的美国一些历史事件中,是可以看到部分结果的。尤其是这种模式是否真的是美国经济能够持续发展不断的源泉,倒是值得思考的。 发明与制造分工也许非常适合于美国的创新环境,然而这种方式,是不是也适合于中国的创新环境,是否也能在当下的环境中,激励中国普通民众的创新,从而将创新转化为生产力,转化为经济效益,实际上是我们应该多思考的。 在这一过程中,中国目前最大的争议并不是“专利可以作为转让的资产”,因为从国家到地方,全部都在鼓励技术转化和专利转化,这一点的国家导向是明确的,是毋庸置疑的。 中国目前最大的问题就是对于NPE这一事务的看待上,而且经常将NPE视为专利流氓或专利巨魔,本身上就存在一定的误区。历史上,还曾出现过动用行政力量来约谈NPE的事件,使得NPE的这种将发明与制造分工的模式,在中国一直处于边缘化和非主流,甚至陷入过人人喊打的状态。 所以在当下,我们要不要拨乱反正,到底应该如何看待NPE在中国经济发展中的历史定位问题,实际上是中国建设知识产权强国的道路上一个无法逾越的关键问题。 因为如果所以NPE的行为都在司法上予以打压,在行政上予以约束,那么中国只善于创新,不善于商业化和工业化的这一部分创新群体的未来之路是灰暗的。 最简单的例子就是我们一直提到的 ,通过简短交流,我们会发现她们夫妇都是非常有前瞻创意的普通人,但是却并不能将其创意产业化。因此,这种创新和发明,到底在社会上最终能否实现对价,实际上考验的不仅仅是这个个案,而是中国整体的创新环境和导向,未来将引向哪里的问题。 实际上,这篇美国的文章,给了我们思考类似问题的一个很好的引子,希望国内对此能有更多的探讨和辩论。 扫码加入知识产权精英社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