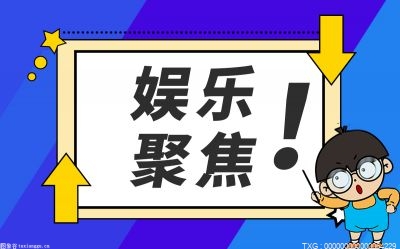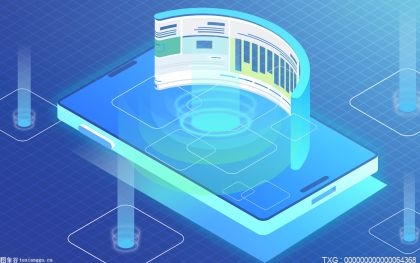(资料图片)
(资料图片)
作者:康兆妮
“白鸽屎”,其实它应该叫花果,在我们童年的时候,是一种奢侈的零食。它小巧玲珑、精致漂亮,五颜六色的外衣,圆溜溜的形状,那香甜的味道,只要一想起,就仿佛弥漫在我们的齿颊,久不散去。
这么好看好吃的零食,我们却称之为“白鸽屎”。这个土里土气的名字,如同村里的小伙伴叫“昂古”“猴子”“黑仔”那样,叫着顺口亲切,有种旁人无论如何也叫不出来的味道。
“小孩,小孩你别馋,过了腊八就是年。”每年腊八一过,村子里的年味便开始弥漫,蒸蒲谷、晒蒲米、炙酒、磨粉、做年糕、蒸粄皮都陆续开始。“白鸽屎”必须是腊月二十四五才进行的,大有挑大梁主角上阵、精彩大戏在后头的味道。
这一天,妈妈天色微明就起床,从阁楼的瓦罐里取出存放的花生米,倒进簸箕,它们在簸箕中滚几番,仿佛从一个不能伸展的狭小空间来到可以自由运动的大空地,快活地滚个不停。那经过精心挑选的花生米,一粒粒饱满滚圆,紫红的外衣发着光亮,不见丝毫的皱褶。
灶膛中,火烧得通旺,大铁锅里的水分被热成水汽,消失得无影无踪。花生米被倒入冒着热气的铁锅中,婶娘用长柄的锅铲不停翻动,花生米像一座小小的山丘被一锹一锹地搬动,最后又重新堆叠成另一座山丘。这两座小山丘不断地变小变大,左右轮换。
另一个铁锅里,白糖被煮得咕咚咕咚地冒着泡泡,像温泉的泉眼那样开着一朵朵微黄的小花。一股被炙烤后的花生米的香气,混合着糖水的甜润,随着空气钻进鼻子,从厨房散发到过道,再到厅堂,弥漫整座屋子,又从烟囱飘散,把整个村庄的空气都变成甜糯的味道。香气越来越浓郁,空气也越来越粘稠,那股香气和甜润就像回南天时的水滴一样,附着在我们的衣服和皮肤上。柴火慢慢地减弱,妈妈捞起一粒花生米放在灶台上,待稍凉后,用手搓开外紫衣,确定花生米炒熟透了。糖浆呢,则用另一个盛着水的碗试火候,用筷子沾一滴糖浆,滴入水中,以糖浆不立即化开,而是沉于水底,为火候刚好。
最后,花生米被全部铲到一个叫“花生托”的竹篾簸箕中,它不同于一般簸箕,无论工艺和用料都极为讲究,要有很深造诣的竹篾师傅才能编织。趁热把糖浆用勺子舀了倒入花生米中,这时候既是“白鸽屎”制作的关键,又考验两个人配合的默契程度。力气较大的扶着“花生托”的边缘,顺着一个方向转动,糖浆沾上花生米就会变成一个个小圆团,随着婶娘不断地转动“花生托”,小圆团慢慢地、均匀地变大。由于温度的迅速下降,糖浆微黄透明的液体凝结成为白色的结晶,又因为不断地滚动,洁净的表面自然形成凹凸点,“白鸽屎”的表面就有了野草莓一样的刺,使得它们拥有一个不同于任何茶点的外部特征。
直到滚动的“白鸽屎”同龙眼般大小就算大功告成,成品“白鸽屎”看起来更像一个个表面有些粗糙的鸽子蛋。小时候,我曾天真地想,是不是它本来叫鸽子蛋,但是被哪位顽皮贪吃、害怕被同伴抢光的小捣蛋故意取了个让人恶心的名字呢?小时候的我们可不管这些名字的来龙去脉,也不计较它的土气,成品一出来,我们就迫不及待地抓一把,全然不顾大人说热气的忠告,直往嘴里丢,边嚼边看着妈妈把黄色、红色、蓝色、粉色的食用色素倒进糖浆,一会儿,“花生托”中的“白鸽屎”就像变魔术一样成了五颜六色。
我们吃着香甜可口的零食,玩着永不厌倦的游戏,跟外乡来探亲的亲戚,不管是自家的还是邻居家的,一一打过招呼,欢笑声、嬉闹声,充满了整个晒坪,蔓延到村庄的每个角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