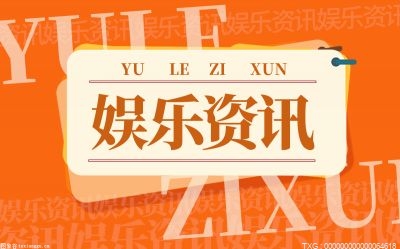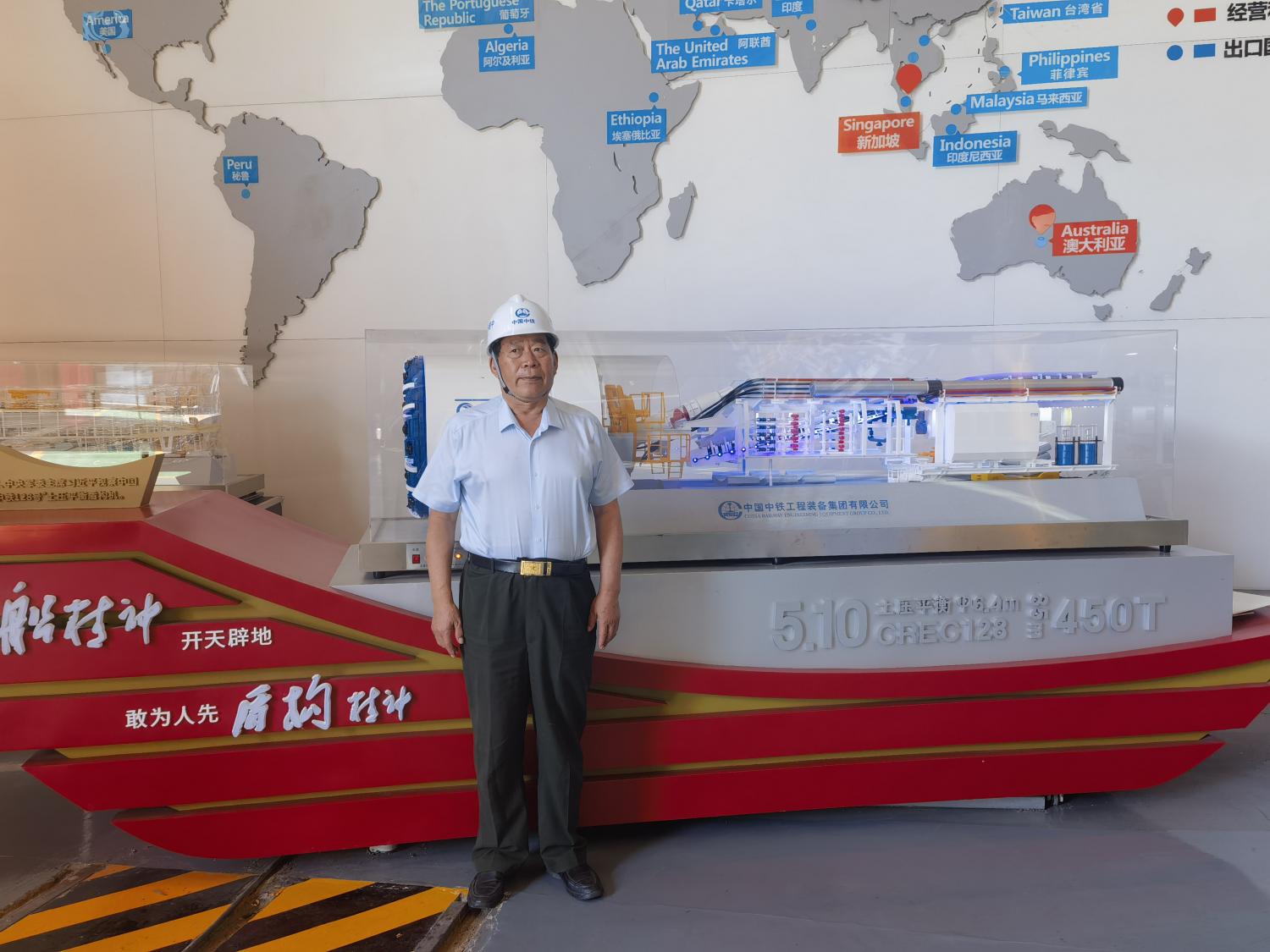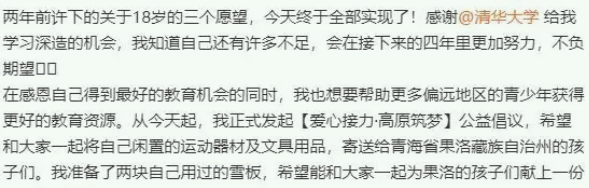采访者:在《玫瑰之名》的附录中你写道:"我在每个地方都能看见中世纪的影子,显而易见地,它们覆盖了我的日常生活,那些看起来与中世纪完全不搭调的生活琐碎,实际上都沾染着中世纪的色彩。"您的那些生活琐事,是怎么沾染上中世纪色彩的呢?
艾柯:我的整个一生,有无数沉浸在中世纪之中的经历。如果你简化巴黎的地图,只选择特定的街道,你真的可以生活在中世纪之中。然后你就可以开始像中世纪的人那样去思考、去感觉。
采访者:你怎么会对中世纪感兴趣呢?
 (资料图片仅供参考)
(资料图片仅供参考)
艾柯:很难说。如果非要我解释,我会说因为这段历史和人们想象的完全不同。对于我来说,它不是一段"黑暗时期",而是一段光明的时期,是孕育了文艺复兴的肥沃的土壤。这是一段虽混乱无序却又生机勃勃的过渡时期——从中诞生了现代城市、银行体系、大学、关于现代欧洲及其语言、国家和文化的理念。
采访者:作为一名研究中世纪的年轻学者,你怎么又做起语言研究了呢?
艾柯:自从我记事起,我就对交流的意义感兴趣。在美学领域,问题是:艺术作品的本质是什么?艺术作品是怎么和我们交流的?我对于后一个问题尤其感兴趣。一方面,我对实验性文学和艺术中语言表现出来的最先进的功能感兴趣。另一方面,我又对陶醉于电视、连环画、侦探小说。
画家笔下的艾柯
采访者:一些反对符号学成为一个研究领域的人宣称,符号学最终会使一切现实都烟消云散。
艾柯:这种立场我们称之为解构主义。解构主义者们不仅假设所有的事物都是文本——甚至这张桌子也是文本——而且认为人们对每种文本都能加以无限的解释,但是他们仍旧遵循着尼采开创的理念,尼采认为没有事实,只有阐释。相反,我继承了查尔斯·桑德斯·皮尔士的思想,毫无疑问,他是美国最伟大的哲学家,也是符号学与阐释学之父。他说过通过符号,我们可以阐释事实。如果没有事实而只余阐释,那还有什么可阐释的呢?
采访者:您曾说"对于那些不可以理论表达的,我们必须讲故事。"
艾柯:这是来自维特根斯坦的一句半开玩笑的话。你的某个想法也许不是独创的——亚里士多德总会早在你之前已经想到。我完全相信,在最终故事总是更为丰富多彩——在故事里,想法在事件中再现、由人物传达、并在精心雕琢的语言中擦出火花。所以自然而然地,当一种想法变成了鲜活生动的个体时,它便成为了完全不同的事物,很可能变得更为传神。
采访者:您的工作是否有条不紊地开展的呢?
艾柯:不,完全不是这样。 一个想法随即会召唤出另一个。一本随意翻看的书会让我想去阅读另外的书。有时我读着一份毫无用处的文献,却会突然想到了一个继续故事的绝妙想法,或者只是想到要将一个小插图盒收进我的插图盒收藏中。
采访者:您是如何努力去做以获得恰如其分的写作口吻?
艾柯:一页文字我要重写几十次。有时候我喜欢高声读出一段文章。现在有了电脑,如今修改完善是那么的容易,也许是太过容易了,因此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变得更为苛求。
采访者:一天中您在什么时候写作?
艾柯:没有定例。对我来说,定一个日程表是不可能的。我总是说我能利用时间的空隙。我们的生活充满了空隙。比如今天早上你按了门铃,然后得等电梯,再过数秒才能到门口。在等你的这几十秒里,我就在思考自己正在写的新作品。我在厕所里,在火车上都可以工作。游泳时,特别是在大海里游泳时我创作了很多东西。
采访者:为什么您要用那么长的篇幅去论述宗教呢?
艾柯:因为我相信宗教。人类是笃信宗教的动物。人类行为中的这样一个特点不能被忽视或者被否定。
采访者:你在米兰这里的图书馆简直就是个传奇。你喜欢收藏什么样的书籍呢?
艾柯:我一共拥有大约五万册书籍。但是作为一个珍藏本收藏者,人类对离经叛道思想的偏爱让我着迷。所以我收集那些关于我不相信的主题的书籍,比如古犹太神秘哲学卡巴拉、炼金术、魔法、虚构的语言。我喜欢那些说谎的书籍,虽然它们并不是故意说谎。
采访者:在你的人生中,知识和文化给了你何种益处?
艾柯:我一直鼓励年轻人阅读,因为那是一种使人博闻强记,发展多样性格的理想 方式。如果你多读书,那在你的人生结束之时,你就拥有数不尽的人生经历,这可是一个别人求之不得的极好特权。
(采访:Lila Azam Zanganeh,原文刊于《巴黎评论》;
中文翻译:五月撄宁、arlene163、香香落野、sibyl玥、独眼一点五,转自译林,有删减。)
✂------------------------------------------